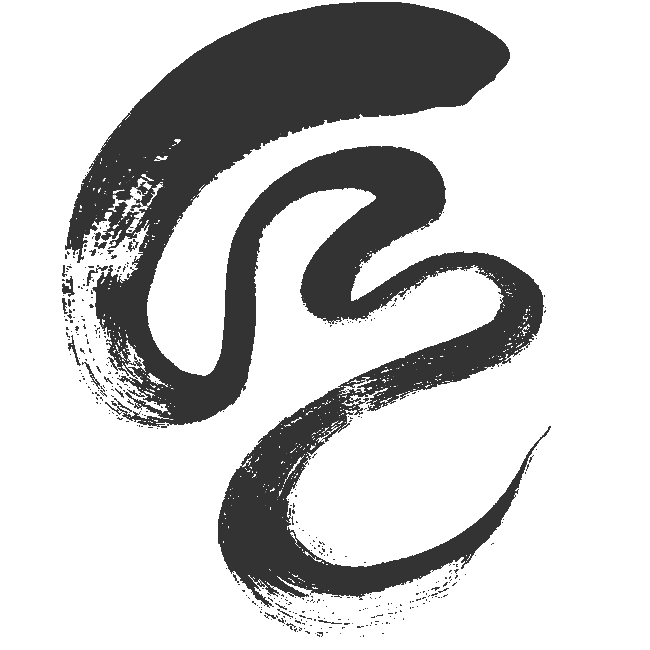平行
叶锦添个展
策展:马克霍本(Mark Holborn)
2016年2月17日至5月16日
法国亚眠文化之家,作为亚眠文化之家五十周年庆典一部分
叶锦添于 2016 年初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举行了展览。这座城市的肃杀冬景,提醒着人们 1 个多世纪前,分裂欧洲大陆的战线正是在这里划下。全球社会在短短 50 年间相继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战后催生了许多防止灾难重演的机构组织。联合国的成立,促使各国扩大相互之间的合作,而几周后随即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体现了全球文化遭遇破坏后,世人对人类文明的强烈保护欲。
随着旧式帝国主义价值观的瓦解,欧洲人民将眼光放远,超越本国边界,投向世界历史文化观。六十年代担任法国戴高乐政府首任文化部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就曾对亚洲文化深感兴趣。年轻时他就在柬埔寨丛林里探索失踪的高棉寺庙。他强烈谴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态度。在他的远见下,一系列 “文化之家”机构不仅在都市文化中心巴黎、更在巴黎之外建立,其中一分支正是于 1966 年建成于亚眠。如今,在这里,叶锦添打造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艺术展览。 他虽向来以中国天才服装设计、美术指导的身份闻名国际,但事实上,他是一名在巨变的时代里跨越了东西方分歧、欧洲旧世界和中华文化新世界边界的重要艺术家。他不仅为了设计研究历史古典传统,同时又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在当代框架中做出不断创新。尽管他是一名为电影和戏剧作品服务的优秀服装设计和美术指导,他那些包括在亚眠展出的服装设计,能超越电影戏剧作品独立存在。作为艺术家,他使用“新东方主义”来概括他创作范围的广度。此次邀请叶锦添前来办展以纪念亚眠“文化之家”五十周年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教皇和沙皇之间的协定下,亚眠这座具有全法国第一大教堂的城市在一战中免于炮火。教堂高高耸立于索姆河之上,相隔几英里远都能看见。作为历史的见证,教堂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时代变迁后,依然保持屹立不倒。二战期间教堂里建造于中世纪的窗玻璃被移去巴黎郊外的仓库保管,没料仓库遭轰炸毁于一旦,却因祸得福:被迫换成透光玻璃后,光线能够穿过教堂窗户直达内部,令原本的朦胧阴暗消失,明亮中夹杂一道道戏剧性的光影——这可是教堂建造者未曾见过的景象。眼观大教堂周围,城市及其农村经历了诸多重建,唯独大教堂作为固定轴不曾改变。
亚眠这座城市,是在索姆河畔建成发展的。叶锦添的展览,在 2016 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 100 周年纪念日前夕开幕。1916年索姆河战役开战首日即有近两万英军阵亡,而整个战役的伤亡人数更达几十万人。这些细节,展览访问者都无法忽视。
一战在欧洲被认为是西方内部之战,但其实那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冲突,战线涉及南大西洋水域、美索不达米亚沙漠、非洲的殖民地等等。锡克教和北非战士同他们的英法战友并肩作战。孟加拉士兵和祖鲁战士也前往欧洲打仗。1916 年英国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输送中国劳工赴法。中国劳工于 1917 年至 1919 年 5 月期间来到法国,停战约六个月后仍有八万中国劳工听命英国指挥。这些劳工中至少有 2000 名死亡,多数死于停战后爆发的流感疫情。索姆河口附近的安静村庄努瓦耶尔,建有官方设立的中国劳工公墓。一望无际的农田旁,这片有围墙包围的土地上,长眠着 838 位中国人,距离家乡 5000 英里之远。公墓由战墓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设计,风格典雅庄重,入口设有刻着汉字的中式坊门。
2015 年夏,我同叶锦添一起赴法考察,其中包括参观中国劳工墓地。一位老村民向我们控诉起英国人的恶行和他们对中国劳工的压迫折磨——看来所有人难免活在历史的阴影中,哪怕出于善意办事也鲜能幸免指控,不可避免地归落于受迫者阵营或压迫者阵营。走在公墓中,看着勒琴斯在公墓中心精心种下的松树,那种简单庄重的设计感中透出悲剧的意味,让我震撼。对叶锦添而言,这番景象一定更具悲伤。叶不仅是一名中国艺术家,彼时更是成长在英国管辖的香港,弹丸地域的幽闭驱使他前往台湾,在那里遇见了电影导演李安,参与了《卧虎藏龙》拿下首尊奥斯卡,之后搬去北京。我看着他穿梭在索姆河旁的墓碑中,痴迷地拍着照,不禁猜测相机是让他看得更清楚了还是起到了与现实隔离的作用。他每天不停拍照,仿佛想借相机镜头让自己在周遭的混乱中斡旋出一席能够立足之地。努瓦耶尔的公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开端。
当我们来布置展览时,叶锦添回到墓地拍摄,这次他带来了Lili。 Lili是这片异地上的旅人,常常同叶锦添一起在欧洲、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现身。她像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十八岁中国女子,几乎总戴墨镜,配有一系列假发和服饰。她的表情既固定又十分灵动。她是一具人体模特,却又是人们深层意识的表达。她是一面镜子、一个暗号、一架工具,生活在现实与另一维度平面的边缘。不论是索姆河边的冬日战场还是亚眠大教堂的寒意内厅,她的出现如同自我意识跨越距离出现在某地观察见证。展览的高潮出现一座高达二十英尺的Lili雕塑,而如胎儿般蜷缩着睡觉做梦的大理石Lili 则是展览的压轴。取名为“原欲”的青铜制裸体Lili,脸颊上滑落以水制成的眼泪,站在迷宫中,呼应着大教堂正中心地上受无数信众们跪行忏悔的螺旋图。而展览最开头,则是一个经解构后支离破碎的大型Lili,躺在似墓室空间的棺石之上,以死亡标志着展览的起点。在叶锦添拍摄的置展花絮视频中,Lili支离破碎地躺在河边沼泽的芦苇丛中,后又出现在中国劳工墓地,身后一具具墓碑,任由雨水鞭打她的脸,断肢间鲜花绽放。
尽管Lili频繁出现在叶锦添的艺术中,不代表叶锦添的艺术被Lili定义。Lili不过是大背景下的一缕细节,在艺术家的伴随下注定发生更多改变,且如同任何成长中的人一样,Lili的变化不会停止。她正要前往上海——这座经历了战乱、象征着历史大背景下不停转变的城市,正躺在古文明发源地的江口,等待着迎接她。